身份與聲音
天空音樂節回來了。自上次去天空,當時辦在金馬倫,高海拔草原上,陰涼清爽的氣候,不時有雲撫過而落下綿綿水霧。我們著得厚厚一層,活蹦亂跳的,依舊感覺不到熱。一班友人,等了老半天的載送車,好不容易來到場合,來追我們剛鍾意的草東,青澀而快樂的回憶。抵達草原的時候,放眼望去,棚頂下擺設好的一排排食肆、攤販,滿綠野上光鮮騎呢、穿著日韓流服飾、口操台灣腔的人們,我彷彿來到一片異邦,一瞬間竟不曉得自身所在何處,要如何與人們溝通,彷彿自己就是異鄉人,誤入了他人的地域。
彼時我固然有訝異,有迷惑:究竟哪個是馬國人,哪個是台灣人?地域與身份,屆時卻一併蒸發。地理位置兩立的人,臨摹著對岸的文化,漫漫南中國海,區隔人與人的疆界,卻在相互模仿而照映的人文中縮短、消融。誠然,身份這東西沒人說了算,當下我卻疑問,究竟什麼是馬來西亞華人?
南洋華裔建立的文化基礎究竟為何?台灣人早在日治時期建立了屬於他們遠東的、繁縟而從簡的文化圖騰。從前下南洋的華人,有自己的一套歷史、有結合南島韻味的宗教、有掺雜古印度的瑰麗與神秘、有游移英治的魍影。可是,年輕一代的馬國華人,泅泳茫茫歷史中,會否找不到一片立足的島嶼?無法在這池子裡尋求認同,而不斷往外借鑒,食用引進的符號,把符號穿在身上、含在嘴裡,最終是否會成為他者?而成為他者,既不是社會中的豎向流動,地理位置上亦無橫向流動,純粹複製了一塊挑揀出來的模式,挪用在一個遙遠的地方罷了。那很多時候,我們一應嘗試與他人分割,兜兜轉轉迂迴於同樣的課題,無窮盡地往裡面挖掘、探問,卻似乎讓障眼法蠱惑了,咋也理不出個所以然。最後回到原點,依舊對身份沒有答案,好比照鏡子,卻照不出自己的映像。
Barasuara是來自雅加達的一隻印尼樂團,首張唱片《Taifun》是印尼獨立音樂多年來少見的精萃。匯合了東西之流,專輯中每隻曲子都熱血澎湃,具富創造力的節奏和吉他音型,甘美蘭Slendro音節與東亞鼓藝的運用,變幻莫測的編曲結構,造就《Taifun》這張完成度極高的作品。時而委婉時而抨擊的和聲,對上意境盈滿的詩詞。聆聽《Taifun》是一次性的體驗,九隻曲目竟系作一首,使人一次聽畢也不覺彆扭。
《Taifun》的可貴在於它對待融和的態度,從中多元、多重的身份頻頻突顯:Pop-rock、藍調、Worldbeat、Prog-rock、電子、東方與西方、現代與過往、男與女,都在聲音中找到共處的方式,每一首歌曲都像聽覺的支點,拉攏著取自世界的萬千,又穩紮自身所有,捏合成一道獨出心裁的景觀。也許印尼人在高度多元的社會裡,文化混沌早已促成新生代面對身份的態度:與其和世界對峙,他們選擇了與之交融。
人類學家博厄斯提出的文化互滲,講的是文化進化史,自古以來人們並非仗著自己發展出文明,文化的散播是在人與人的交匯中,群體與群體的會合中交換而萌生變化的。生於南洋的華人,植根於此的人,擁有無數屬於本土的,親近的符號,是否擁有塑造自我的無限自由?是我們探索未竟,抑或是我們拒絕了這道找尋自身的門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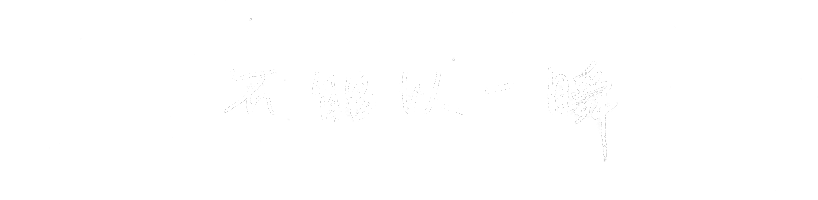

留言
張貼留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