無感
無感, 外面很暗/ 現在這個病,開始有人死了、人都害怕,還禁足,不能出門更怕/ 我已經好久沒有反芻反芻我的內裡,哪些情感知覺/ 他們可能囤在裡面很久了,很亂了,像把卡帶膠扯散/ 可能我一直以為這樣擱著,不去理他,一切就會好/ 我沒有想到會突然有一天,事情就這樣發生,一個人被迫站在鏡子面前,重新觀照自己/ 這個人,他是/ 很久以前我當作我知曉一切,我決定隔離,在意識與現實之間畫線/ 因為那時候的我,那時候的那個人認為世界究竟空虛,所有貼身的人、世間煙火,都是傷心的源頭/ 不去想,自然就不會傷心了。’ 我沒有想到會突然有一天,事情就這樣發生/ 人們全部被困在房子裡面,遲早痴線/ 他們發了部隊警察出來巡邏,抓在外面繞的人/ 我們坐在黑黑的陽台,我出來拿毛巾被嚇到,一團人影和他的酒樽/ 我們都很失望,很心痛/ 為什麼可以這樣把心託給一個人,然後任人搾碎/ 上次他分手躲在房間哭了兩天,我沒有去過問/ 現在坐在陽台上,坐在我面前哭/ 我也揪心/ 是不是沒有可以信任的人呢,是不是沒有人值得被愛/ 是我不相信愛/ 感情這種東西,很蹊蹺的,讓他進來,接受他,接受他的不是;然後他糟蹋的時候,塴堤的時候,全都自責/ 是我們太輕易受騙,輕易騙自己嗎/ 這時候我們都想知道 可是受傷的人,一屋子受傷的人/ 因為我們把自己敞開任人毆打,現在就三更半夜睡不著,寫字/ 唉, 是不是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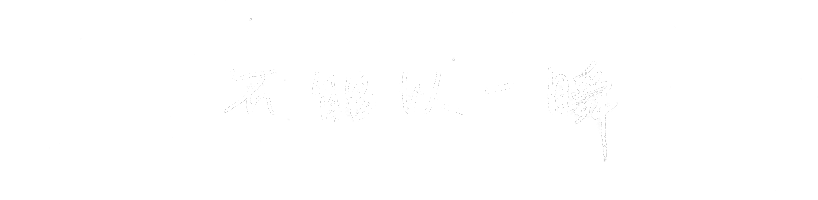
.jpg)